荆州楚墓出土玉器略论
春秋战国楚墓以及属于楚文化系统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反映出楚人对玉的极度喜好和楚国玉石琢磨工艺的高度发达。楚人好玉和楚国玉石琢磨工艺的发达,是与楚地悠久的玉文化传统分不开的。就考古发现的楚国玉器来看,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可知,玉石琢磨是楚文化体系中的一大要素,楚国玉器集中体现了中国先秦玉文化发展的成就。
一、楚国玉器的地位
玉器所体现的玉文化,在中华文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之一,就是中国先民在原始社会晚期创造了发达的玉文化,而且发展至今,形成特色鲜明、蔚为大观的玉文化系统。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曾经说:“世界上别的古代文明中,除了中美洲文明外,都没有玉器。”
玉,在中国人民心中是高尚、珍贵、美好的象征。我们的祖先在很早就说过:“玉,石之美者,有五德。”还说:“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以玉之德喻人之德,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道德观念。中国成语中有无数以玉为典来形容人的美德的词语,足见玉在中国的传统道德中有多么的重要。玉器在中国礼仪制度中,也是最高的礼器。比如王国维就认为,契文中的礼字,就像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物中,玉就是供奉神灵的器物。
中国最早的玉器发现于距今约8 000年的内蒙古兴隆洼文化遗址。在其后距今约6 000~5 000年的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也发现了玉器。过去以为玉器的制作最早起源于北方。实际上,南方长江流域的先民也很早就制作玉器了。长江下游距今约7 000~5 0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就出土了玉管、玉玦等玉器;距今约5 000~4 000多年的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玉琮等大量玉器,则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玉文化发展所达到的高度。长江中游距今约4 600~4 000年的石家河文化遗址也出土了许多造型新奇、制作精细的玉器(图一)。

图一 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玉神人
河姆渡文化遗址和良渚文化遗址都在鼎盛时期的楚国疆域内。石家河文化因今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而得名,其遗址群所在地就在距楚国故都纪南城东北不远处。
楚人对玉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从历史上的著名典故“完璧归赵”中可以反映出来。世人都知道这块赵国玉的珍贵,但这块玉其实并不是赵国自产的宝物,而是出自楚国,后来被楚王作为聘礼赠给了赵国。和氏璧就是以一位楚人的名字命名的。此人就是春秋时期出生于楚地荆山的一位叫做卞和的石匠。这个故事不仅表达了玉的精神,还颂扬了卞和和蔺相如的如玉般忠贞的品德。同时,故事也说明当时楚地的荆山产玉,而且玉的质量还相当好;还说明楚人对玉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从开始的不识宝,到后来将玉当作珍宝。而且楚国制玉的工艺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以至于制作的玉器被当时各国视为宝物,争相收藏。楚人好玉、识玉且工于琢玉,楚国也盛产玉器,楚国高级贵族的墓葬中均有精致的玉器陪葬。
楚人对玉的钟爱,在历史文献或者民间流传的故事中也有反映。《左传·昭公十三年》记载,楚共王有宠子五人,本应该立长子做继承人,但共王举棋不定,有人出主意由神来决定。于是,共王与夫人巴姬将一块玉璧秘密地埋在宗庙庭院里,让五个儿子轮流来拜,只要能碰到埋在地下的玉,就可以继承王位。后人嘲笑共王卜嗣埋璧是荒唐之举,其实这正是楚人对玉的灵性的崇拜导致的举动。但后来事也凑巧,这五人与王位都有了些许关系。老大去世不久,老二杀死老大的儿子,当上了楚王;老三老四和老五串通一气发动政变把老二赶下了台,纷乱之中,老三老四自杀,老五自立为王,并得以善终。这一结果有意无意地验证了玉作为占卜之器的灵验,说明玉在楚人心目中是神灵的替代物。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后世有不少怀疑,然而我们只要从故事中能够了解玉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就足够了。
荆门包山楚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楚国设有专门的机构——玉府,说明楚国已经把制玉当作官府的一件日常事务,足见玉器在楚人生活中的重要。
由于知道楚人钟爱玉,诸侯中的小国有时为了巴结楚王,也会把自己国家好的玉器作为礼物,送一些到楚国,以博得楚王的欢心。
二、石家河文化的玉器

图二 罗家柏岭遗址出土玉人头像
荆州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玉器是在天门石家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1955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天门石河镇罗家柏岭遗址发掘,发现了少量的玉器,有人头像(图二)、蝉、龙形环、凤形环、璜和管等。这些玉器的造型都比较粗糙,而且玉的质量也很一般。1981年,考古队在荆州肖家屋脊遗址的探方中发现了一批密集的瓮棺葬。肖家屋脊北边与罗家柏岭遗址相连,荆州博物馆在钟祥六合地区的石家河遗址中清理了25座瓮棺葬,发现多数瓮棺葬中都有数量不等的玉器和玉的残片,总数达20余件。种类包括人头像、蝉、管、笄和坠等。这些玉器究竟是少量的陪葬物,还是大量的陪葬物呢?是一种偶然的陪葬还是已经成为墓葬的习俗呢?它们是这一地区共有的现象吗?带着这些疑问,考古工作者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和发掘,希望能挖出更多的玉来证实楚地玉器的大量存在。
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考古工作者再一次对石家河遗址进行了发掘。1988年冬,先是发现了一座瓮棺中陪葬着一件玉鹰和一些玉的碎片。这一发掘成果使大家大为惊喜,于是便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在之后的发掘中,他们又发现了一批密集的瓮棺墓。在这些瓮棺中,出土了与前面发掘的玉器类型相当,而种类和数量却要多得多的玉器。在一座瓮棺中,出土了56件玉器,种类不仅包括前面已经见到的玉人头、玉蝉、玉鹰和玉璜等,还有虎头像、龙、管、坠等多种玉器。这些玉器不仅可以证明荆州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存在大量的玉器,这些玉器的制作水平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而且还可以证明这些出土玉器与此前发现的罗家河玉器有某种联系。这里实际上存在着一系列以玉陪葬的习俗,因为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的。在发掘的玉器中,有一件雕刻完整精细的虎头像,还有一件玉笄上端的方棱柱上浮雕着一只鹰,雕刻得也十分精致。
有了这一次有价值的发掘后,考古工作者信心更足。1988年12月,考古队同时开始发掘两座大型瓮棺墓。发现了精雕细刻的晶莹剔透的管型玉人头像。它造型独特,显示出人神一体的风格。这是石家河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器之一,人头玉器的面部虽然各具表情,但都神情肃穆,穿戴整齐,耳朵上还佩戴着耳环,颇似巫觋式的人物,或者就是供人们膜拜的对象。墓中还出土了足以确定墓葬性质的器物:红陶杯和陶罐,说明这批瓮棺葬就属于石家河文化,这与1955年定性的石家河文化正好相合。
这样的玉人头像过去在国内别的墓葬中也曾有发现,但都无法断定它的年代,但这一次肖家屋脊出土的玉器廓清了历史的迷雾,把这种精美玉器的制作年代展现在我们面前。
玉蝉是石家河文化墓葬中出土最多的一种玉器。这些玉蝉都带有双翼,蝉体长方形,一般长2至3厘米,头部、吻部突出,眼睛呈椭圆形,雕刻得十分精致和逼真。
玉虎头像(图三)也是石家河文化中出土较多的玉器,数量仅次于蝉。有一个玉虎头像雕刻于一块较薄的玉片上,虎额顶有三个尖状突起,中间有一道竖凸棱,耳郭近似树叶形,耳角还向上方突出,鼻梁宽大,显示出了老虎的基本形态。
玉飞鹰也是石家河文化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种玉器。图四是一件圆雕的作品,鹰身长1.9厘米,双目圆睁,呈展翅飞翔状,钩喙圆眼,背上还浮雕有羽毛纹。该器玉质光洁、雕工精美。

图三 肖家屋脊出土玉虎头像

图四 肖家屋脊出土玉飞鹰
在石家河文化的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玉龙。它造型独特,龙体首尾相卷,几乎相连,上颌尖,下颌短,口微微张开,与后世的龙相比,显得更古朴、抽象。也许这就是江汉地区龙的雏形。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除了自身的特征之外,有些玉器与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有相似之处;同时良渚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中的代表性玉器——琮,在这里也有发现,说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已经不是单纯土生土长的地方性产物,而是受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
石家河肖家屋脊考古队从1987年到1991年在肖家屋脊共进行了8次发掘,发现了各种类型的丰富的玉器,共计157件。这些玉器与1955年在石家河罗家柏岭发掘的玉器属于一个时期,一种文化类型,是楚地最早的玉器。
荆州地区出土的数量众多、种类丰富的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已经基本具备了中国古代玉器的几大功能,如礼仪功能、实用功能、陪葬功能、陈设赏玩功能等。

图五 枣林岗遗址出土青玉人头
1990年冬,江陵马山枣林岗遗址发现了46座石家河文化的瓮棺葬,其中的43座墓都有玉器陪葬。这些陪葬的玉器与肖家屋脊出土的玉器大体相同,也有玉人头(图五)、虎头、蝉、鹰、龙等动物形象玉器,也有首饰和生活用具的玉器,如坠、管、珠、簪,和玉礼器琮、璧、璜等。其中玉人头的形象更为逼真,雕刻得也更为精致。而且这件玉人头用料考究,显得晶莹剔透。人头上似乎还戴着一顶帽子,头的轮廓和五官也更为清晰精致。还有一件鹰首的棕玉玉笄,为别处所不见,可能是女性的首饰用品,雕刻得也十分精妙美观。
三、荆州楚墓出土的玉器
如果说荆州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只是长江中游玉文化雏形的话,那么,荆州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玉器就应该是楚文化的成熟之作了。这样一些成熟的玉器,除了在20世纪60年代荆州望山2号墓和雨台山墓中有少量出土以外,有幸在近几年被考古工作者大量发现。它们的出土地点就在离肖家屋脊和枣林岗不远处的荆州川店熊家冢。熊家冢墓是一座大型的楚国墓葬,无论从规格气势还是从陪葬的器物来看,都应该是一座楚王墓。
在主墓尚未挖开时,已经清理了36座陪葬墓,这些墓葬应该是主墓主人的姬妾或者侍卫,在被赐死后,埋在主墓主人的周围。陪葬墓应该有90多座,但目前只发掘了一部分。墓中的棺椁尸骨均已不存,但在放棺椁的位置上却都摆放着成组的玉器,玉器是这些墓葬的主要陪葬物(图六)。各墓出土玉器的数量不等,一般出土十几件到几十件。比如1号墓出土的玉器由这样一些玉器组成:11件玉璧、1件谷纹玉璧、4件素面玉珩、1件四龙二螭形玉佩、1件六龙形玉佩、7件紫晶珠和1件水晶环。而纵观所发掘的墓葬,玉器器形主要有玉璧、玉璜、玉珩、玉佩、水晶珠等,还有一件十分精致的水晶扳和一些水晶和紫晶的珠子。

图六 熊家冢墓地玉组佩出土情况
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玉器不论用材、形制和雕刻都比新石器时代有了很大进步,如双龙形的玉璧,龙的形状更加具体,器体上还雕刻有精细的花纹,有浅浮雕的卷云纹,有透雕的蟠螭纹,还有谷纹、勾连纹等。一条长龙形的玉佩,颜色为米黄色,龙作回首扭身、蹬足摆尾状,眼、鼻、角上有线形的刻纹,相比原来的龙来说,熊家冢的龙还有了足,足上还生动地刻出了龙爪,这已经与现代的龙没有多少差别了。这件龙形玉佩把龙的曲折蜿蜒和贵气都体现出来了。熊家冢墓中的玉龙有不少是双龙(图七),还有龙凤合刻在一件玉器上的龙凤玉佩(图八)。龙呈曲颈、蜷躯、卷尾状,龙体周边有隐形的阴刻云纹;凤依附于龙的尾端,喙为钩状,身上刻有羽状纹。颜色为青绿色,并杂有不同颜色的斑点。这些玉龙让我们看到了楚文化中除凤之外的另一种古代灵物的大量展示。
与龙比起来,凤的身躯要小得多,只在龙的尾部占据一小块地方。相比楚墓中大量出土且地位颇高的凤来说,玉器中的龙显然占据着主要的位置,显示出龙的霸气,而凤的位置十分有限。这其中的含义有待于今后深入的探讨。

图七 熊家冢墓地出土双龙玉璧

图八 熊家冢墓地出土双龙双凤玉佩
在熊家冢出土大量玉器的同时,荆州其他地区也出土了毫不逊色于这座楚王墓的玉器。
1997年,荆州马山镇一战国墓地被盗,文物局在接报警后派考古专家进行抢救性发掘。虽然残存的随葬器物已不多,但仍发现了由玉覆面(图九)、玉瑛和玉佩构成的一套完整的头部葬玉。玉覆面与人的五官正好切合,双眼和鼻孔都是镂空的,面、眼、鼻、耳、发、眉等部位的轮廓线和发、眉、髭的线条都是用阴刻手法雕刻的。雕刻的手法熟练细腻、线条圆润流畅。人面的比例也掌握得恰到好处。整个覆面给人的感觉就是神态安详自然,眉清目秀,没有常见的墓葬中陪葬品面目都比较狰狞的特征。

图九 秦家山二号墓出土玉覆面
中国的丧葬活动中有用覆面和裹首的习俗,两周到汉代的玉覆面虽然发现不少,但基本上都是以小块的玉连缀起来做成的。而荆州秦家山的玉覆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用一整块的玉刻成,覆面的轮廓为上宽下窄的椭圆形,发髭也是中分式的,与荆州出土的木俑的形制基本相同。可以认定,这块玉覆面是荆州地区土生土长的玉器,但也是参照了早于它的中原地区的缀玉覆面而做成的,由此可见楚人善于学习也善于创新的传统风格。
如果说秦家山楚墓出土的玉器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征的话,那么荆州马山镇院墙湾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则是让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的精美工艺品。
2006年3月,荆州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对马山镇的楚墓群展开了一场抢救性的发掘。墓葬被盗得很严重,墓内几乎空无一物,所幸在坍塌且灌满淤泥的棺椁内还有些没有被翻动的遗物,于是考古工作者便着手清理这里的文物。让人欣喜的是,大家的辛苦与努力没有白费,由于淤泥的保护,棺内的一些珍贵文物有幸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包括28件精美的玉器,有回首龙形玉佩(图一〇)、龙凤玉佩、神人龙凤玉佩(图一一)、玉璧、玉环、玉璜等等。

图一〇 院墙湾楚墓出土回首龙形玉佩

图一一 院墙湾楚墓出土神人龙凤玉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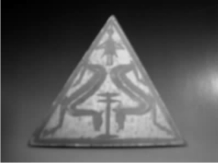
图一二 院墙湾楚墓出土双鹿飞鸟玉印
与其他墓葬中只葬礼仪玉器、实用玉器和玉首饰等相比,这座墓葬中发现了一方玉印(图一二)。玉印的两侧边各刻着一只鹿,顶端刻着一只正面的飞鸟,正准备展翅高飞。其纹饰为抽象的花纹,但一眼就能辨出是鹿和鸟的形状。这块玉印是做什么用的目前还不得而知,但与已发现的其他种类玉器明显不同。
这些玉器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玉材也选得非同一般,以青玉为主,还有少量白玉。玉器的纹饰有云纹、蝌蚪纹、圆首尖勾纹、谷纹、龙凤纹、网格纹、平形线纹、菱形纹和绹纹等等。雕刻的手法也有多种,有阴刻、减地、浮雕和透雕等等。院墙湾1号墓是继望山2号墓以来荆州地区出土玉器造型最独特、工艺最精美的战国楚墓。
四、楚地玉器的功能与意义
荆州地区出土的先秦玉器,从新石器时代的石家河文化玉器,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玉器,无论从种类、风格还是形制方面,基本上都是一脉相承的。楚国玉器,既有楚国自身创造的特色,也有受北方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玉器在楚人生活中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它在楚人生活中的地位如何呢?
按玉在古代的功能,人们一般把玉分为这样几种:礼玉、葬玉、首饰玉、生活玉和作为兵戈的玉,具有宗教功能、使用功能、装饰功能、社会等级功能等。楚墓中出土的这些玉基本上已经具备这几种功能了。

图一三 熊家冢墓地出土玉璜
古代祭祀所用的礼玉专指璧、琮、圭、璋、璜(图一三)、琥。荆州楚墓中出土了璧、琮。圭,则出现在文献记载中。楚国有一等级称为执珪,表明楚人已经有了专门用于祭祀的玉器,并且祭祀的玉器后来衍化成政治等级的标志。璧这一祭祀中首选的玉器,在荆州楚墓中是出土数量多而且地位高的一种。璧有各种不同的花纹,多为扁平的圆形,中间有一较大的孔。璧的花纹一般都琢磨得很细致,花纹也多种多样,但大多为谷纹、回纹和涡纹。而且越到后期,璧的工艺越精致,用材也越好。璧在比较大型的墓葬中都有出土。在荆州熊家冢的陪葬墓中,它也是成组玉器中的一种。
琮,是一种外方内圆的粗管型玉器,也是用于祭祀的玉器。与璧一样,琮在楚墓中发现了不少,大约是死者生前的祭祀用品,而死后因为也要顾及阴间的鬼,所以就连着死者一起下葬了。
作为人死后陪葬的物品,玉也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不仅在荆州,在整个发掘出来的楚墓中,绝大部分都陪葬了或多或少的玉器。这些陪葬的玉,有些是专门做成用来陪葬死者的,有些是日常生活中的玉器,死后也随葬了。比如玉琀、玉握、鼻塞、玉覆面等就是专门用于随葬的。荆州仅秦家山墓葬中出土有玉覆面,没有发现其他葬玉。在古代墓葬中,琀、玉握和鼻塞的规格比玉覆面要低得多,出土琀的墓葬可以有很多,而出土玉覆面的墓葬却寥若辰星。这种玉覆面不仅工艺要求高,而且对玉材的要求显然也是很高的,它需要用很大一块玉石才能刻成。这是死者身份地位达到一定程度的标志。作为陪葬品的玉器,还有为数不少的动物形玉器。用玉雕刻成动物形进行陪葬,是古代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反映。他们要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生活了,于是要带去各种生前的生活用品,由此用动物形玉器来陪葬就产生了。
楚国贵族的生活是比较讲究的,在楚墓中经常可以发现为数不少的各类首饰和装饰品,如金、银、铜、漆器等等,而玉器更是显示贵族生活质量的一种宝物。这些作为日常生活中装饰用的玉器,包括首饰,也是荆州墓葬中出土玉器的一大类,比如佩的数量就为数不少。佩是古人随身佩带的一种装饰品,在屈原的《楚辞》中就有不少贵族身上佩戴各种装饰品的诗句。荆州出土的佩大多都制作得十分精致,有些则达到相当的高度,比如人操凤鸟玉佩(图一四)、多首龙形玉佩(图一五)、龙凤形佩等,从石家河文化到战国墓葬,佩的发现呈数量逐渐增多、工艺逐渐提高的状态。楚国贵族十分看重身上的这种玉佩。据《左传·定公三年》记载,蔡国国君昭侯献给了楚昭王两件佩玉和两件裘服,后来楚国还为争夺此物引发了一场大战,显示出玉器已经成为楚国贵族钟爱的宝物,并会不择手段地对玉佩进行追逐。除了佩以外,装饰品还有环、簪、玦、管、珠等等。装饰品除了工艺上的精致、造型上的多变以外,用材上的多样也是它的一大特征,荆州出土的装饰品中,除了用一般的玉石外,还有绿松石、水晶和玛瑙等玉材。多种玉材的使用正印证了《楚辞》所说的楚人好奇服、喜欢美物的观念。

图一四 熊家冢墓地出土人操凤鸟玉佩

图一五 院墙湾楚墓出土多首龙形玉佩
楚人尚武,以玉器制作的兵戈不仅成为祭祀时武器的象征品或替代品,也常常成为贵族们日常佩戴的物件,当然也用来陪葬。墓葬中常常可以见到玉剑,其形制与战争中所用的剑、戈、刀不同,从大到小、从抽象到具象变化多端,表明楚人已经把用玉制作的武器仅仅当成是武器的象征或者干脆就是一种装饰品。但这种玉兵器往往只陪葬在男性的墓葬中,由此可见它的作用仍然是十分鲜明的。
荆州楚墓中出土的如此之多的玉器,所用玉材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要制造这么多的玉器不可能完全依靠外来的材料,当地一定有玉石。卞和献玉虽然是一传说,但荆山之地产玉却是真实的事实。有学者考证了《山海经》中对水的记载,证明长江、汉水、漳水、沮水流域周围的山脉都属产玉之山,其中以荆山为首,这正好与卞和寻玉的荆山相合。湖北还是绿松石的产地,绿松石是制作玉器的一种常见玉材。荆州楚墓中出土的灰色、白色和绿色的玉都是用绿松石制作的。而呈黄色、茶色和墨色的玉则是用河南南阳出产的南阳玉制作的。这块地方就是早期楚文化的发源地,因而那里的玉传到春秋末直到战国都是楚国腹地的荆州是顺理成章的事。这就是荆州楚墓为何多出玉器的原因。
荆州地区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而且楚国在春秋末到战国时期的都城就设在此地,此时正是楚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因此这一时期墓葬出土的玉器也显示出楚文化的鲜明的发展轨迹。与荆州地区所出土的其他楚文物一样,玉器也显示出楚文化发展到了顶峰。




